
“……在一艘无人驾驶的船上,乘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到底是谁在驾驶着这艘船,看起来好像无人驾驶。’……
“‘这艘船本来就是自动的。’……
“‘这艘船可能是永恒的,机器的各部分碰巧就合在一起了,没有经过任何工程师的设计就自然形成了。’……
“……又有人叫道:‘我不要到其它地方去,我只想留在这里!’
“……但船上的大多数水手及乘客的心里却被另一个较为实际的问题所占据:‘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最后要在哪里登陆呢?’”
这是林语堂先生《信仰之旅》一书中描述人类信仰起点的一幅图画,他称之为“近代世界的写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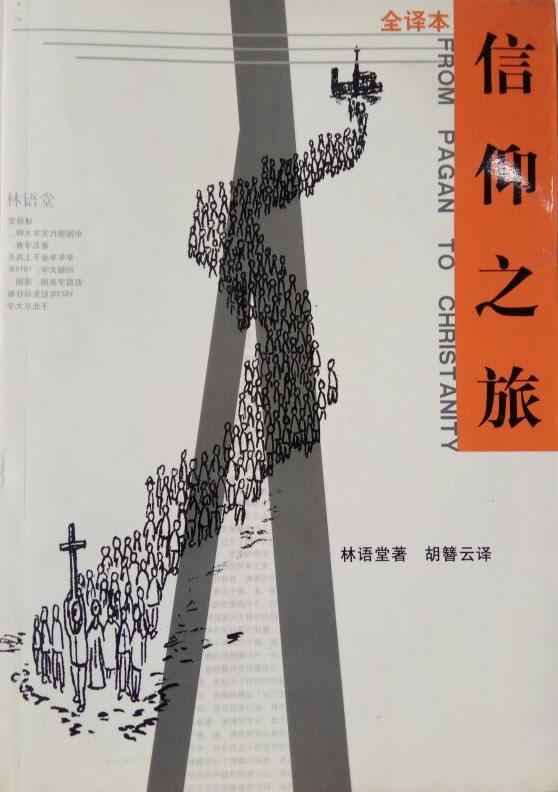
在我孤陋寡闻的印象中,中国的文学家、思想家或科学家很少有从容自如地撰文来深入讨论宗教信仰问题,而比较世界各宗教之高下异同,甚至专门著文谈论自己个人信仰经历者,则更是闻所未闻。
所以,当我读到《吾国吾民》(大陆译本《中国人》)和《京华烟云》的作者这本讨论信仰问题的著作时,着实讶异了一番,这确属凤毛麟角之作。
人生,诚如林先生所言,是航行在茫茫无际的汪洋大海之中的一艘巨轮,甚至在你还不知道时你已经在船上了。你不知道这艘船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似乎看不到船长和水手,不知道谁在掌舵开船,这艘船怎么会一直往前开呢?为什么不停一下再开、开一下又停、开开停停?甚至,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翻船呢?
但是有多少人认为这样的问题对我们个人的“灵魂”是重要的呢?又有多少人认同我们是在一条人类共同的“生命之船”上呢?我们很少真正踏上《信仰之旅》,执着地追寻这一人生最重要问题的答案。我们也许对《吾国吾民》更感兴趣——因为那是有关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形象”。
林语堂先生是福建一位基督教牧师的儿子,他是民国初年中国最优秀的跨国文化学者之一。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学士学位,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相继在清华、北大和厦门大学任教,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科主任、世界笔会副会长等职,并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正由于林语堂先生学贯中西、又有亲身登临信仰群峰的特殊经历,是名副其实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今古文章”的第一人,才使他晚年的这部著作别具特色。
但林语堂先生在探索这一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时,并非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那里指点江山;或只是一个凑热闹的外行人在“为赋新诗强说愁”;也不是以学究权威的角色对宗教评头论足;而是以在“这艘船”上一个乘客的身份,试图寻索自己所乘的“这艘船”的来龙去脉。
林语堂心中的“信仰”或“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件他和上帝之间的事…… 是一次灵性上充满震惊与遇险的旅程”。“这本书是一个人探索宗教时经验的纪录。记载他在信仰上的探险、怀疑及困惑;他和世上其它哲学及宗教的磋磨,以及他对过去圣哲所言、所教最珍贵宝藏的探索。”
林语堂以一个思想家特有的“探险、怀疑及困惑”的精神,用主要的篇幅先后穿越了“孔子的堂室”、“道山的高峰”及“佛教的迷雾”,然后转向“理性主义”和“ 物质主义”,对它们向宗教信仰的挑战予以回应。最后,他遇见了耶稣那耀眼炫目“威严的大光”,那照亮人生航向的云上的太阳。
在这一趟旅行中,他最关切的是“人的灵性、生命的理想及人类的品性”。
林语堂以孔子为起点,开始了他的“灵性的大旅行”。很显然,孔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所不在,孔子的“克己复礼”统治了中国将近二千五百年。为此,林语堂认为孔子可能是“所有历史中最成功的社会哲学家”。“孔子代表道德的中国”,而孔学儒士则“成为古代中国知识阶级的贵族”。

由于孔子对于社会纲常教训的影响,使他“对上帝及上帝意旨的关心,及他对于宇宙的灵性性质的看法,被儒家的实证主义所蒙蔽”,而林语堂则想考察孔子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态度。
“上帝——或天,如孔子所了解的,是严格独一的神,但在民间信仰中,则有许多神祇。有一次有人问他:‘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而孔子回答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有一次病得很厉害,有人建议他‘祷尔于上下神祇。’孔子回答说:‘丘之祷久矣。’
“论语记载他所最‘慎’的事情是‘祭’及‘斋’。换句话说,孔子假定上帝是高高在上的,用神秘微妙的方法来领导人事的进行……他一生的历史研究十分注意古代宗教祭祀的方式。”
另一方面,“孔子是个教育家,对藉个人的修身来改革社会有兴趣,……‘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孔子在处理人类社会问题时是把个人放在社会之上的。”
有意思的是,林语堂特别将孔子与马克思作了比较:“我想起孔子和马克思刚好是采取对立的观点:孔子相信没有人格改造的社会改革是表面的;马克思则以为社会环境决定人的道德行为,而乌托邦的实现要靠物质环境的变换。过去四十年间苏维埃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正足以证明后者的假定带来了多少灾祸。由于人类对权力的同样的野心和贪婪,领导者之间的嫉妒与无情,人类为生活舒适及权力斗争必要付出忍受不平等的代价……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并不解决人性的问题。今天在苏维埃联邦的男男女女和联邦外的人一样,为同样的动机所支配,以父母之心关怀他的子女,想送他到比邻近的儿童所进的更好的学校,他们同样以赚钱为工作动机,想得到较高的待遇,也同样有阶级和特权的欲望。私有财产及继承权已经恢复。阶级的特权及工资的不平等已稳定地进展。假以时日,这个反常的俄罗斯国家将坚定地向资本主义社会‘前进’,甚至容许自由工作、自由思想及自由旅行,虽然她仍飘扬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对人性妥协,而不是人性对社会主义妥协。”
半个世纪前中国的林语堂,几乎就像两个世纪前法国的托克维尔一样,预言人性的力量,是任何国家政治、思想、主义等意识形态所无法彻底摧毁的。
孔子著名的“仁”,有“慈爱”的意义,“在孔子则指最好的人,是人性发展到理想的圆满。”林语堂发现,“‘仁’字的发音刚好和‘人’字一样,因此一个仁人,读起来是‘仁仁’。这使我们想起英文有一个相似的例子,就是 human 及 humane 两字意义的相似。英文的 humanity 一字,像中国的‘仁’字,包含有‘人道的’及‘人性’的双重意义,例如‘基督的人性(humanity)’,而‘仁’在哲学上的发展则成为具有‘真人性’的意义。”
但是针对孔子以个人的修身养性和礼仪来规范和改造社会的“礼”学,林语堂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一个人,除了想做一个好父亲或好儿子之外,就永远不想做其它事了吗?一个人还清了债务,把儿女送入市内最好的学校之后,不会再问我是谁?或者我应该如何生活吗?人是真的满意了,还是在他心灵深处有些不为人知的疑问呢?诸如我是谁?这个世界是怎么开始的?世界之外还有什么?……”
这就是站在中国文化精神另一端的老子对中国的贡献:他给予中国一个俯仰天地的超越视角和潇洒境界。
老子曾对孔子予以忠告:“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彻底地洗净你自己,除去你一切仁义德性;你就可以得救。”这使得林语堂联想起耶稣几乎相同的教训:“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林语堂认为:“孔子让自己的心灵和上帝本身保持距离。孔子凭着良知说:‘未知生,焉知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些话是无法令一个仍然被逼要跳出这种‘可知’的知识范围,宁冒痛苦或失败的危险去追求未知的人满意的。它也不能使我满意。”
“儒”与“道”,林语堂视为是中国思想对立的两极:“孔子是一个实证主义者,而老子则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孔子最关切的是人,而老子最关切的是宇宙的神秘和性质;孔子视宇宙为人的一部分,而老子则认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
对孔子和老子这两位中国文化精神的巨人,林语堂作了进一步发人深省的比较:
“孔子教人以一种德国人的极端严肃和恳切的决心来生活;但在中国人的灵魂中常有来自老子的深思,及可怕沉默的忍耐力,对权威的缄口顺服,定意忍受一切痛苦,枯坐以待任何暴君自毙的伟大的无抵抗,无论这些暴君的势力是多么大。”
“道家与儒家,不过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一个是属于活动的、有作为的、相信的一面;另一个是属于静观的、怀疑的、惊异的、使生活笼罩着一种如梦性质的一面。”
“当一个中国人成功的时候,他是一个儒家;当他为艰难及失败所围困的时候,是一个道家。”
“那些被踢出办公室的官员,……当他是一个重要的内政部长时(即他还是一个儒家的时候——作者注),可能常常忍受失眠之苦,现在却他睡得很香,因为他是睡在道家的天地里面。”因为“官员像孔子,而作家及诗人像老子及庄子,而当那些作家及诗人成为官员时,他们表面上像孔子,骨子里则仍是老子及庄子。”
林语堂对老子的智慧和思想极为推崇,称他为“世界上第一个深藏不露的哲学家……老子充满似非而是的隽语;老子则把他深奥的智慧挤入光辉密集的五千宇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用这么少的字来具体表现一种哲学的全貌,且曾对一个民族的思想有这么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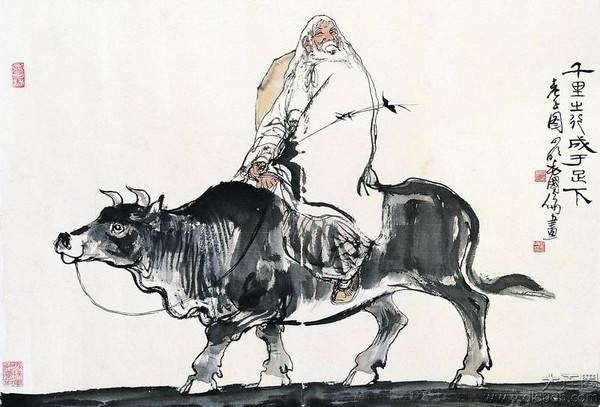
他认为,“老子的影响是大的,因为他充实了孔子积极主义及常识所留下的空虚。以心灵及才智而论,老子比孔子有较大的深度。”
老子思想的中心是“道”,这“道”是一切现象背后的大原理,是生命起源的原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它像流注到每一个地方、滋润万物而不居功的伟大的泉源。道是沉默的,弥漫一切的,且是隐藏不可见的,但却又是无所不能的万物的原始。”
老子的“道”实在很接近写于老子之前一千多年的圣经《创世纪》中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的“话”——道。只是老子说他不知其名,曰“道”。然而无独有偶,《新约圣经》则直称“道就是上帝”。
林语堂甚至进一步发现,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救赎的真理“用老子以下面的句子来表现,其相似之处,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如反。’”
“老子……在精神上几已升到耶稣的严峻高度。……老子对爱及柔和谦卑的力量的训言,在精神上和耶稣那独创卓识、闪烁着光芒的训言相符合,有时连字句都惊人的相似。”这是林语堂对老子的结论。
而对老子的传人庄子,林语堂的激赏之情溢于言表:“庄子是我所爱好的…… 因为他的风格的迷人与他思想的深奥,他无疑地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散文作家;同时照我的评估,他也是中国所曾产生的最伟大及最有深度的哲学家。”
虽然林语堂先生钟爱老庄,但在他结束“道山的高峰”行程之后,却不无遗憾地感叹道:“从老子智慧的高峰降到民间道教的神秘学、法术、驱邪逐鬼,从来没有一个宗教退化到如此地步。今日道教道士最大的用途是赶鬼。如果哲学家拒绝制造神,民众常自行想象制造他们所需要的神。中国思想中最固执的倾向是相信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及它们的相生相克。”
在对独具“中国特色”的儒、道学说进行深入探讨之后,林语堂的目光开始转向了“对古代中国的思想和心智唯一的外来影响”——佛教。

拥有浩瀚繁复的经典轶卷、经由帕米尔高原和西藏高原进入中国的佛教,被林语堂先生称为人类思想信仰的“迷雾”。林语堂认为,尽管历史上“中国学者极其卑视道教及佛教,将它们视为绝对迷信,但以一般人对宗教的认知,中国人可以说都是佛教徒。”因为“无论学者阶层怎么想,中国人民却需要一个流行的宗教,要有一个神来向他祷告,有一个天堂来盼望;在较高尚的意识中,他们也需要罪恶的忏悔,从痛苦、疾病、仇恨、贫乏,及死亡中被拯救出来的方法。”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梁武帝四度出家,靠亿万银两几度赎回,却使其皇朝国运逆转;“自大狂”武则天伪造佛经、僭称佛身临凡;著名的唐三藏在去阿富汗及印度十六年后带回了六百五十七部佛经;而民间老百姓竟慢慢将一位男菩萨观世音变形为一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女观世音菩萨——佛教以其独特的方式最终成为中国本土“宗教”。
我想起林语堂在他的《吾国吾民》中曾说过:“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产生神奇的镇定作用。”而“在对待人生的消极态度上,佛教只是道教的一种狂热的形式罢了”。
当然,佛的世界要比中国民间“变形金刚”式的耽想要精妙复杂得多,连最有思想的学者都不得不敬畏三分。
比如说,物质世界是“没有”——空的“存在”:“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 沤灭空本无,况复诸三无?”
比如说佛祖的大弟子文殊甚至警告另一大弟子阿南要抵抗记忆,因为记忆会堕落为斜思淫念:“阿南从强记,不免落斜思”,即使是记住佛的教训也是如此。
“佛努力在禅上成功的目的,是想成为某种温和的超人。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已消灭他自己的知觉心,而因此消灭空间与时间的概念;他已升到脱离一切有情及精神拘束的自由地位,而从一种超感觉的心的本质(就是佛性的本身)来看望这个世界及人生,他就是超人。”
当然,这些都是非常人所能理解或感悟的。而禅的境界,到最后“只是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谜语,或是一个巴掌和一吐口水。”
佛要使“一切人类经验非人类化,以致达到一种像神一样的稳定、宁静、和平,如迦叶所说:‘身常圆满紫金光聚’”——佛的本身。
但是,如果记忆(人类的一切思想活动都基于记忆能力)是不可靠的,思想是无益的,生命是“空”的,世界是“幻”的——“生性有如空,缘生故如幻”,那么还剩下什么呢?“打坐”、“入定”、“修行”以致“涅磐”是否最终也是不可靠、无益和空幻的?
在这里,林语堂以并不常见的严苛态度发问评论道:“当然,佛是很感动人的,但这位大师同时又教导我们人的思考是无益的,它犹如‘自咬肚脐’一样徒劳无功。那么为什么还要什么天台宗及华严宗?… 这是我对一切宗教、特别是佛教所想说的:如果宗教是意味着超脱凡世的,我反对它;如果宗教是意味着我们必须从这个现世知觉生活中出走,且有多快就多快地‘逃避’离开它,像一只老鼠放弃快要下沉的船一样,我是和它对立的。”
与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最大的儒、道、佛相比,唯物主义无神论则是当代个人心灵和精神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彻底的无神论在林语堂看来“完全是一个特殊时代人造的产物,只限于一种思想的特殊方式。与一般的信仰不同,唯物主义很少能够成为一个思想家对宇宙问题逻辑推理的根据,而往往是当情况开始显得不太正常、扑簌迷离甚至混乱之时,那些见风使舵和走捷径之人所采取的立场。”
在林语堂的眼中,唯物主义在二十世纪的趋势将逐渐形成“道德的犬儒主义:人性的优美及光明已经过去……任何人若不赞赏毕加索画里挺着大肚子和笨重大腿的怀孕妇人,就是毫无希望的反天才的无知者。于是毁灭的时代来临了,毕加索以一个把钟表拆开,得意地将轮子、指针、螺旋钉及弹簧抛在自己面前的顽皮孩子的心情,切分着这个物质的世界,称它为‘内视’……每一个人都撕破一些东西,而以这样的行为来接受群众的喝采。”
“什么东西被毁灭并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破坏,因为只有藉着破坏,人类才能表示自己‘进步’。”
而在这一“全面的破坏”中,林语堂特别注意到佛洛伊德“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他把图书馆设在厕所里面,以便于分析许多关于人的事情。”以至于现在任何人要进行对“人”的研究和分析,都必须到“厕所”里去进行。“佛洛伊德要说什么,他就自创什么语言:他发现“灵魂”一字被滥用,就非常聪明地用‘精神’一字来代替。接着便是‘本能的冲动’、‘本我’、‘自我’及‘超自我’,最伟大的词当然是‘下意识’……佛洛伊德派对于人类灵魂的报告,事实上刚好和一个公爵堡垒里面的女帮厨的报告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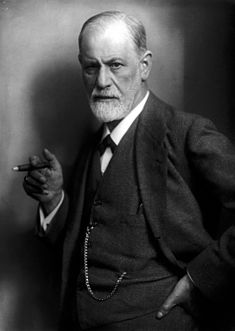
弗洛伊德使“人心和人体已再没有什么隐私;心理学的学生们已经剥去了无花果树之叶,吹散了一切秘密。已经把赤裸的、正在发抖的灵魂送到厨房的洗涤室,而把厕所改为公共走廊;他们已使爱的魅力钝化,把罗曼司的酒弄酸,将尊贵的羽毛拔去,使人内心的至圣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高坛上推下来,而让发出恶臭的‘本能冲动’戴上皇冠坐在它的宝座上。”
可见,林语堂对二十世纪唯物主义对道德人心带来的祸害深恶痛绝。
而对中国人来说,林语堂认为(孔子)的“人文主义已经继续了将近二千年,没有任何人对唯物主义的哲学让步。中间只有过一个活在主后五百年左右的无神论者范缜(梁武帝时代——本人注)。中国人始终是哲学上的理想主义者——重视道德过于物质,而一般民众,则宁愿崇拜偶像或诸灵,也不愿要一种僵死、无神的唯物主义。”
至于二十世纪科学的发展,也使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走到了尽头——林语堂称之为“穷巷”:“近代原子及电子的发明,不只是改变了人对宗教或生命的看法,而是推翻了一切……物质原来是无以名状的、百万伏特的能量驾驶着忽隐忽现无限小的电子……对于物质的传统观念已无法坚持,物质不是固定的,事实上物质是空的,而且并非始终可见。……这些发明的结果是‘物质让位于心灵,而不是心灵让位于物质’。”
“自然科学家像是一个忠实的向导,他把你带到可知世界最边缘一道关闭的门前,坦白地告诉你:“此门之外我不知道,而且无法告诉你。”因为科学只能显示物质世界是“什么”或是“怎样”,却不能显示“为什么”。
与马克思自称其理论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的态度相比,林语堂认为达尔文还较为谨慎,较有“科学精神”,但对其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却毫不犹豫地提出了鲜明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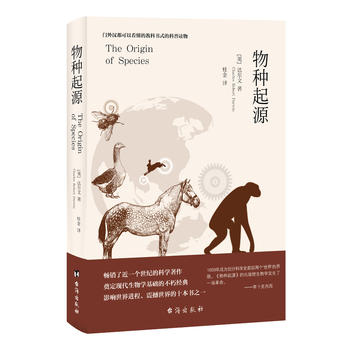
“‘物种起源’其实是一种信仰,一种易于招致质疑的直觉猜测,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我不知道,没有科学家可以确知,但在这个‘信仰’中有几个概念上的难题。
“在赫克尔的手中,这个信仰无疑地已变为一种美好的、几乎是诗一样的结构——被称之为‘生物的奇迹’。但以一种学术理论而论,进化论就像一个幸运之轮,被给以无限的时间盲目的碰机会来搅出对的号码,那就不免漏洞百出。”
林语堂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赌场的赌盘作比较:“我希望看到一种可理解的学说,一位有资格的人告诉我(他的资格不能差于长期流连在蒙地卡罗游乐场的人),在他一生中,曾看见过一次连续搅出五次零的号码。我自己曾见过连续搅出三次零的号码。在轮盘赌中仍未有人看见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号码连续按次序出现。也许在一百万年中这样的情形会发生。但把生命科学的理论建立在这种盲目碰机会的基础之上,听来却令我震惊。盲目碰机会的意义是靠“运气”,而一个拥有庞大形体的宇宙却靠“运气”而建立,听来盲信多过客观的科学。如果在一个赌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号码按序出现,外行人健全的反应,是怀疑赌场主人有意作弊。”
林语堂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在这里,他进一步发现:“在这种‘瞎碰机会’的理论中,其实有许多矛盾。第一,它假定一个有机体是因它‘适应’了某种目的而生存,但其实最终却‘适应’于没有目的(盲目)的目的(进化)。目的的存在或不存在变成纯粹是形而上的(空谈),而所谓进化也只是为了一种没有目的的目的而改变,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无法理解;
“其次,常态(物种)并没有被进化的过渡形态的化石所支持,甚至在百万年的化石中也找不到……缺乏证据,于是就不得不杜撰说,人是从一道没有梯级的楼梯下来,或从有梯级而没有连接东西支撑着它的楼梯下来的;
“第三,叔本华进而推测有‘适应的意志’……(就象)在一个堆满五百张锯形谜板的盘子,在无限次自动变化之后,这些谜板终于各就各位一样。这只是一个奇迹,而科学不能像奇迹。
“其四,永恒的变化是不可理喻的目的论。……根据瞎碰机会的理论,蛇制毒液并不需要思想,不过需要在千万分之一的机会中瞎碰。而与有效射击毒液的舌头及毒液囊的系统配套,也只需要万万分之一的偶然巧合。但因偶然的侥幸继承这种能耐而使下一代也能在体内准确地形成这一化合物的可能性,又要去碰十万万分之一的机会。一种如此简单的东西,以一次碰机会再加上随后要碰的机会合并计算,将是一之后跟着廿三个零分之一,或 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但依靠数学上的或然率是相当危险的。而这种机会必须发生在我们能有一条有毒的响尾蛇之前。生存是容易的,但得到这种机会却是难上加难。这难道真是科学吗?”
由于进化论以“科学”之名出现,使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得以在全世界蔓延,以致在精神、信仰和道德层面,“我们现在停留在悬疑及无知中。”
林语堂强调人类理想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道德的混乱是违背人的本性的。我认为人喜欢有一种强有力的生活理想。一个有清晰理想的社会,要比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更易于生活的。它产生较少的神经衰弱者,较少的挫败感,及较少的精神崩溃。”
对于马克思主义,林语堂认为,“像厄塞尼女皇的装饰一样绝对正确的马克思,缺乏谨慎(伪科学态度),以致使他的每一教条都面临着一千种事实的挑战。”

林语堂对共产主义国家“无神宗教”的观察是严苛的,但也是深刻的:“在莫斯科及北平苏维埃领袖们无所不在的画像,宣告了即使在一个无神的社会中也有对某些神祇或其它东西崇拜的必要。……不幸的是,那个他们曾经向他崇拜了卅年之久的神,死后按照赫鲁晓夫所说,变为一个杀人凶手及阴谋诡计的主谋。一个歹徒,二万万人崇拜了他卅年之久,竟未能发现他的真相,就让我们称它为历史上的偶发事件吧。虽然如此,在一个无神的社会中,一神主义必然永远继续,这个宗教无误的“主”是马克思,它的“启示先知”是列宁。如果这个“启示的宗教” 不像神圣一样被崇拜、被坚定地高举,整个无神教会就会崩溃。”
“这就是我们所到达的虚无。”——虚无的信仰。
十九世纪以来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狂风暴雨猛烈地冲击着人类这艘“航船”,迫使它改变既定的传统航向。有思想的人都对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行径、以及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及红色恐怖对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但是信仰之光被无神论的乌云遮盖,道德价值被随意颠覆,人类希望的前景被虚无主义的黑暗笼罩。
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呢?人类的希望在哪里?
“不是在那可怕的黑暗中,已经有大光来拯救人类了吗?”林语堂在他的心灵深处,发出了比黑暗更深沉的呼喊!
“我曾在甜美、幽静的思想草原上漫游,看见过某些美丽的山谷;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曾爬登道山的高室且看见它的崇伟;我曾瞥见过佛教的迷雾悬挂在可怕的空虚之上;而也只有在经过这些之后,我才登临基督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达云上阳光普照的世界。”
林语堂一生游历中西文化和思想,亲身体验不同信仰体系及其影响。他在基督教家庭成长,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探求并沉浸于各种信仰和文化之中,成为他自己称之为的“异教徒”。他对当时一些教会和基督徒行为的批评是严厉的。当他晚年回顾自己信仰沧桑时,他悚然注目的却仍然是耶稣基督那穿越人类历史黑暗乌云的“威严的大光”:
“耶稣的世界和任何国家的圣人、哲学家、及一切学者比较起来,是阳光之下的世界。像在积雪世界的冰河之上,而且似乎已接触到天本身的瑞士少女峰一样,”
与孔子、老子、庄子和佛陀的教导相比较,林语堂认为,“耶稣的教训直接、清楚、又简易,使每一个想认识上帝或寻求上帝之人的其它一切努力都相形见绌。……在耶稣的世界中包含着力量及丰富——光的绝对无限的明朗!在这里,没有孔子的自制,佛的心智分析,或庄子的神秘主义。在他们推理的地方,耶稣施教;在他们施教的地方,耶稣命令。
“耶稣道出对上帝最完满的认识及爱心。耶稣传达出对上帝的直接认识及爱慕之感,并进一步直接了当地指出,对上帝无条件的爱及遵守他诫命的行动就是彼此相爱,平等相待。如果一切大真理都是简单的话,我们现在就是站在一个简单的真理面前,而这个真理,是一颗包含着人类一切美好发展原则的种子!”
林语堂的信仰之旅,使他曾经攀登人类不同心灵智慧的高峰。但当他重新审视耶稣基督,探讨他个人魅力和力量来源时,仍然发出带着他那特殊的思想火花的问题:

“将耶稣与其他一切人类导师相比较,他那种独特的、炫目的光茫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如爱默森所称道的耶稣吸引人的魅力是从哪来的呢?”
林语堂发现,“耶稣说话不像任何导师那样说话。耶稣从来不解释他的信仰,从来不伸明它的理由。他以了解知识的平易及确信的态度来说话。他教人不用假设也不用辩论。
“他以极其自然和优美的态度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他以十分朴实的态度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声音,一种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声音。
“他有一种真正高贵的声调:“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一种二千年来浮现在人了解力之上的命令的声音。”
林语堂的信仰之旅当然是十分个人性的,但是作为一位跨越国界文化、博古通今的一流学者,一位关注“人的灵性、生命的理想及人类的品性”以及中国及人类前景的文化和思想大师,他的信仰历程不仅仅是个人性的,对中国人的信仰和心灵世界也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林语堂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一个道德犬儒主义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人类理想的崩溃付出代价……一切社会主义的改革,只是倾向和注重于物质和经济的研究,其实正如庄子所说‘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及孔子所言‘声色之于化民末也’。”
面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泛滥使人类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道德底线的现实,林语堂坚信“我们所需要的是深度,而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深度。”而这个深度只有“直接追随耶稣教训的核心”才能获得,就象法国著名的历史学者勒南所言:“耶稣为人类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道德的最高原则。”
林语堂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耶稣的教导不仅是属于灵性的,而且具有强大的政治性——正是耶稣的信仰导致了当今民主和自由的政治体制——“这种自由民主的世界性宗教的根源来自耶稣的道。” 因为在耶稣的话语中,“人的基本价值被肯定。”
唯物主义者“相信只要给那些最卑微的人有饭吃,便万事大吉了。”但耶稣却向世界宣告:“‘天国就在那些饥渴慕义的人心中’、‘温柔和谦卑的人将承受地土’,前者赐人心灵内在的自由,后者宣告‘我弟兄中最小者’(最不起眼的人)的价值。换句话说,谦卑的人在心灵上是自由的,而最谦卑的人将会获得胜利。”
林语堂认为,这正是“一切自由和民主背后的灵性原则。”“因为这个原因,人类将永远崇拜他,无论他曾是何等卑微。人基本价值的淳朴教义,将继续被证明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力量。”
“今天,这种力量仍然是充满活力,它常常更新以沉默的革命来推动人类进步。更奇妙的是,耶稣的教导从来不为任何思想、主义和物质经济的概念所动”,却影响着整个世界和各个时代。
“在耶稣无与伦比的教导中,有一种令人信服的、人所能听到的最崇高的人生理想。人们常常以为耶稣对上帝的启示是过去的事,然而今天无论谁读《福音书》都会相信这是上帝在今天明确无误的启示。……基督徒一旦在他们的生活中‘结出果子’,就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抵抗基督教改变人心的力量。”

对于耶稣在人类历史中无可比拟的影响,以及他对人心灵永恒的震撼力量,即使身为文学语言大师,林语堂也情不自禁地、一再引用勒南那美丽优雅、惊天动地的激情文字:
“这位崇高的人物,每天仍掌控着这个世界的命运……伟大的创作力将会再出现,这个世界会因由古代勇敢的开创者所开辟的道路而满足吗?我们不知道。但无论将来无法预料的现象如何,耶稣将永远不会被超越。对他的崇拜将常常更新新的一代,他的生平故事将不断使人流泪,他的受苦将使最善良的心灵也软化;世世代代将在自己的子孙中宣扬他的名字,比耶稣更伟大的人物将永不会产生。
“安息在荣光中——高贵的创始者: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你的神性已经建立;不必担心你努力构筑的大厦会因某一条裂缝而崩溃;从此以后,在脆弱的人类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你从你神性和平的高处,彰显你无限的能力和影响。几个小时苦难的代价,甚至完全不能触及你伟大的心灵,你已经赎回最完整的永生。千万年后,这个世界仍将颂扬你。我们反抗的大旗,也只会成为环绕着你而进行的激烈战争的记号。自从你死之后,你比你在这个世界行走时更活跃一千倍,更可爱一千倍,你已成为人性屋隅的首石,那些想把你的名字从世界除去的,将会被彻底震垮!”
我们仍然处在人生之航的苍茫虚无中,但是我们可以“将蜡烛吹灭,因为太阳已经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