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哲学简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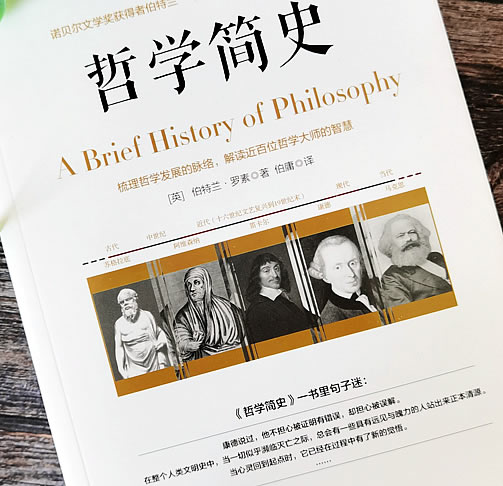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首次出版于二战结束的1945年,在二十世纪曾是一部名噪一时、影响颇大的哲学史“名著”。虽然从学术角度来看,作者不够严谨和随意性的倾向比较明显,但在当年充斥着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和反基督教意识形态的西欧及中国学界,这部全面介绍西方哲学、行文流畅、並时有出奇不意及具挑战性观点和评语的著作确实受到青睐。
我在当年自由思想被全面封锁的共产主义世界曾将罗素的这部著作当作了解西方哲学和世界思想史的指南来读,尚具启蒙意义。但如今再读时,却恍若隔世,不禁为罗素扼腕长叹:没有信仰之人的愚昧及其对世人的误导是何等之大!即使是这位在此书出版时已七十三岁、受过“良好教育”、闻名遐迩的英国贵族科学哲学家,与我这个在文革中长大、没受过什么教育、第一次读此书时才二十来岁的懵懵懂懂的青年共产党员对基督教信仰、上帝和世界来源的看法竟然没什么两样。
这本貌似温文尔雅的学术著作,事实上充斥着我之前所熟悉的可怕的、非理性的无神论观点,弥漫着顽固的反基督信仰的世俗气息,误导着人类思想知识界的认知,可谓是今天泛滥全球的左派思想在二十世纪哲学界的先声。
作为公开宣告自己是一个不信者的罗素,他是如何试图从无神论的角度来阐述基督信仰来源的呢?
他将充满内在矛盾、彼此对立的希腊哲学作为西方思想史的起点和轴心,却将无论对当时还是今天人类历史社会和心灵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的基督教信仰的神学思想任意肢解,将肢解后的一部分胡乱塞进希腊神话和东方秘密宗教的木乃伊之中,将另一部分塞进五花八门的希腊哲学派别之中,只是为了否定基督信仰是来自真神上帝的启示,为了证明基督信仰只不过是来自希腊和东方宗教哲学的拼凑。
请看罗素是如何对基督信仰作开场白的介绍的:
“在巴比伦的大地女神伊什塔尔,希腊殖民者在小亚细亚为她建筑神殿的时候称她为阿尔蒂米斯,这就是‘以弗所人的狄阿娜’的起源。基督教又把她转化成为童贞女玛利亚……”
“基督教把一个早已为斯多葛派学说所包含了的、然而对古代的一般精神却是陌生的重要见解给普及化了。我指的就是认为一个人对上帝的责任要比他对国家的责任更为必要的那种见解。象苏格拉底和使徒们所说的‘我们应该服从神更甚于服从人’的这种见解,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以后一直维持了下来……”


作为学者的罗素开宗明义就如此轻率地将圣经中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童贞女玛利亚混同于以弗所虚无神话中的女神狄阿娜;而且在罗素这位数学逻辑哲学家的眼中,基督教就是她自己一直反对的异端——希腊哲学派别中最具泛神论倾向的斯多葛主义的翻版(罗素在书中另一处又提及斯多葛主义也是伊斯兰教的翻版),这显而易见不符合逻辑。他又将《使徒行传》中彼得的名言“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与苏格拉底《克里托篇》中的“公民服从”混为一谈——苏格拉底的服从是对国家法律的服从,而彼得宣告的是对至高上帝的服从,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但罗素却把他们混同于一回事,只是因为他们都用了同一个词:“顺服”。
罗素认为基督教“神学是一种武断的信念”,它产生了“一种无知,并对宇宙产生了一种狂妄的傲慢”。从这种武断的信念和狂妄的观点出发,罗素“神秘地”发明了属于自己的无知和傲慢的“酒神神学”,将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通过奥尔弗斯(又译俄耳甫斯)的神密宗教和柏拉图哲学——与希腊神话中放荡不羁的酒神狄奥尼索斯联系了起来:
“狄奥尼索斯…这个神…多少是一个不名誉的酗酒与酩酊大醉之神。由于对他崇拜便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神秘主义,…甚至对于基督教神学的形成也起过一部分的作用……”
“在希腊……有些哲学家基本上是宗教的;这特别适用于柏拉图,并且通过他而适用于后来终于体现为基督教神学的那些发展。狄奥尼索斯的原始崇拜形式是野蛮的,在许多方面是令人反感的。它之影响了哲学家们并不是以这种形式,而是以奥尔弗斯为名的精神化了的形式,…奥尔弗斯教徒是一个苦行的教派;酒对他们说来只是一种象征,正象后来基督教的圣餐一样。”
就这样,罗素完成了否定圣经是神的启示的证据收集,武断地证明了基督教信仰就是希腊哲学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派、犹太道德历史观、酒神狄奥尼索斯和奥尔弗斯教等东方迷信宗教的大杂烩:
“天主教哲学,就我使用这一名词时所含的意义而言,是指由奥古斯丁到文艺复兴时期为止支配着欧洲思想的哲学……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哲学,亦即天主教教会的哲学……后期罗马帝国传给蛮族的基督教包括三种要素: 一,哲学的一些信念,主要是来自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但在部分上也来自斯多葛学派;二,来自犹太人的道德和历史的概念;三,某些学说,特别是关于救世的学说,它们在部分上虽然可以追溯到奥尔弗斯教和近东的一些类似的教派,但他们在基督教里大致上却是新东西。”
但是这符合逻辑吗?一个了无新意、靠着希腊玄渺哲学和迷信宗教拼凑改装而成的宗教竟然能统治西方两千年,成为人类最强大的文明体系,难道像罗素这样的逻辑哲学家没有看出这有一点不符合逻辑吗?
我开始对罗素同志的理解能力产生严重怀疑。因为罗素在书中对一个十分明确的、有关圣经文献的重大历史事件都不能直截了当地陈述实情,却对其闪烁其词:
“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希腊化的程度比犹太境内的犹太人为甚,他们甚至忘却了希伯来语言。因此他们只得把旧约全书译成希腊文,其结果便是旧约圣经七十人译本。”

但已知的历史记载并非如此。《圣经七十士译本》是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为建造当时世上最大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而专门请求耶路撒冷召集12个支派各出6人共72位圣经文士学者(长老),将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这在当时就有记载,之后与耶稣处于同时代的著名犹太哲学家菲罗有更明确的历史记载。在主前第一世纪前完成的这一希腊文圣经译本,成为主后第一世纪在罗马帝国疆域中基督福音迅速广传最重要的文本基础。事实上,这是上帝为基督福音在罗马帝国迅速广传事先所做预备的明证。是什么样的不信才会导致罗素要罔顾事实歪曲历史呢?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闭口不谈圣经对西方社会的思想和精神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闭口不谈圣经不容质疑的神圣源头,却大谈特谈被公认为伪经(伪经——几乎所有人都不认可、无人能证明其真实性的伪造书籍)的《以诺书》和《十二先祖遗书》,并且暗示福音书抄袭了这些伪经:
“对于基督降生不久以前的犹太文学毫无所知的人,最容易把新约全书看作一个崭新的开端。但事实并非如此。先知的热情,为了赢得世人的听闻虽然不得不设法伪托古人,但是这种热情却绝对没有死灭。在这方面,最有趣的是《以诺书》。”
罗素的意思就是,福音书中许多基督的教导实际上是抄袭《以诺书》的,也就是说,无数基督徒们为之被迫害了300年、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福音,并非是使徒和门徒们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记录,而是抄袭了一部当时就没有什么人相信的伪造文献。罗素真不愧为一位只有想象力而无理性逻辑的二十世纪“逻辑分析哲学家”。

罗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将宗教改革时期英国的清教徒也归为柏拉图主义者:
“清教徒为什么要反对音乐、绘画和天主教会的繁文缛节呢?你可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十篇中找到答案。”
当然,无神论者的本质就是离弃和敌视基督教信仰及圣经原则,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这方面的典型。罗素的这种现代左派特有的篡改和自编历史所伴随的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在书中比比皆是。他一方面高抬希腊哲学,将其置于基督教神学之上,为的是要说明基督教信仰并非神圣的启示,而是来源于希腊哲学和神话;另一方面当他面临为什么希腊哲学连在希腊境内都无法成功而基督教却能在欧洲全面发展这一问题时,罗素却不从希腊哲学和神话的角度来回答,而是又一次“王顾左右而言他”:
“基督教的成功是因为“基督教的团结与纪律。”
如果共产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觉得奇怪,但是罗素?
提到共产党,罗素却又将基督教信仰直接间接地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挂上了钩:
“犹太人对于过去和未来历史的理解方式,在任何时期都会强烈地投合一般被压迫者与不幸者。圣奥古斯丁把这种方式应用于基督教,马克思则应用于社会主义。为了从心理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运用下列词典:
耶和华 = 辩证唯物主义
救世主 = 马克思
选民 = 无产阶级
教会 = 共产党
耶稣再临 = 革命
地狱 = 对资本家的惩罚
基督作王一千年 = 共产主义联邦”
我想罗素大师对自己的这种“创意”一定十分满意。罗素的这种荒诞不经的历史观我倒是十分熟悉,因为这与不讲逻辑理性和常识真理、只讲辩证法和诡辩术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如出一辙。尽管罗素当年就已经注意到了他同时代的苏维埃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将基督教信仰彻底“消灭”了,但他却不知道、也不可能预料到,就在他自己死后不过二十年,当强大无比的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苏维埃忽然间分崩离析、自由重回人间之时,那些曾被专制压制和束缚的人们,也在一夜之间再一次回归并拥抱他们祖先的东正教信仰,那是罗素不能理喻、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相悖的信仰,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信仰。今天,俄罗斯至少拥有超过1亿的东正教徒。

而罗素却像是一个幼儿园玩乐高积木的孩子一样,在最肤浅的层面上将基督教比作共产主义,(或者)然后再反过来玩。罗素和马克思的区别在于他们的结论: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而罗素则认为人类哲学的出路在于他的逻辑分析哲学。不过,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马克思和罗素两人都错了,而且错得十分离谱,错得几乎不着边际。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显然是人间地狱;而罗素认为哲学可以通过逻辑学最终发现和解释世界本质的努力,则被“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证明完全是徒劳的理论空想。
作为哲学家和数学家的罗素,在对自己生活其中、对人类哲学和科学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西方文明的思想基础——基督教信仰全面抹黑的同时,不知为什么却对崇尚暴力专制、在历史上对人类哲学、科学和伦理道德毫无建树的伊斯兰教极尽谄媚和献殷勤之能事,不仅对它们千年来对基督教文明(包括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东正教文明)国家的军事侵略和劫掠历史及其造成的巨大破坏轻描淡写,还篡改和歪曲历史,为其涂脂抹粉,毫无根据地口口声声称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对保护和传承希腊文明做出了贡献:
“公元七世纪,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们征服了叙利亚、埃及与北非;下一个世纪,他们又征服了西班牙。他们的胜利是轻而易举的,只有很轻微的战斗。除了可能在最初几年外,他们也并不是狂热的;基督徒与犹太人只要纳贡,就可以安然无恙。阿拉伯人不久就接受了东罗马帝国的文明,…他们的学者阅读希腊文并加以注疏。亚里士多德的名气主要地得归功于他们;…阿拉伯人在哲学上作为注释家,要比作为创造性的思想家更优越。对我们来说,他们的重要性就在于:唯有他们(而不是基督徒)才是在东罗马帝国被保存下来了的那些希腊传统的直接继承人。在西班牙…与回教徒的接触才使得西方知道了亚里士多德;…从十三世纪以后,对希腊文的研究才使人能够直接去翻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是假如阿拉伯人不曾保留下来这种传统的话,那末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也许就不会感觉到复兴古典学术的获益会是那样地巨大了。”
罗素的这一段叙述,就像共产党的宣传一样,竭尽歪曲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之能事。历史的背景和事实是,从伊斯兰教帝国第七世纪向基督教世界开始军事进攻的八百年间,基督教(希腊东正教)世界大量的希腊学者在不断逃亡,少数学者在伊斯兰军事占领后被捕、被杀、被奴役、被迫改变宗教信仰、被迫改变姓名后,不得不成为伊斯兰帝国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学者和被迫“纳贡”的二等公民,有些为伊斯兰帝国做翻译,其中一些是犹太人。这些“二等公民”和“臭老九”被回教世界炫耀为他们“智慧之家”的财富,被罗素这种盲目的一厢情愿的现代学者称为“回教学者”。
事实上,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一个正统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在历史上对希腊哲学留下任何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著作。我们只要读一读罗素自己在书中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所写的自相矛盾的“赞词”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回教世界独特的文化,虽起源于叙利亚(基督教会的发源地之一——本文注),却随即盛行于东西两端:波斯与西班牙(原因:这两个地区都离回教中心最远,而且各自本来都有自己的宗教传统——本文注)。叙利亚人在(被回教)征服期间是亚里士多德的赞美者(这说明叙利亚的基督徒才是希腊哲学的传承着——本文注),奈斯脱流斯教派重视亚里士多德过于柏拉图,柏拉图是为天主教徒所喜爱的哲学家。阿拉伯人最初从叙利亚人获得希腊哲学的知识(这说明阿拉伯人对希腊的所谓贡献,原本就是来自叙利亚的基督徒——本文注),因而从一开始他们便认为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为重要。然而他们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却披上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外衣(显示阿拉伯人对希腊哲学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的无知——本文注)。金第(约死于873年),这个首次用阿拉伯文写哲学的人(言外之意:阿拉伯之前没有哲学——本文注),同时也是阿拉伯人出身的唯一著名哲学家(证实了阿拉伯没有其它著名哲学家),翻译了普罗提诺所著《九章集》的一部分,并以《亚里士多德神学》的名义刊行了他的翻译,这给阿拉伯人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带来了很大混乱(普罗提诺是著名的柏拉图主义者,是西方哲学界公认的新柏拉图主义之父,却被阿拉伯最著名的哲学家误以为是亚里斯多德主义者,这证明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世界根本没有罗素所吹嘘的希腊哲学的底蕴,更遑论贡献了——本文注)。阿拉伯哲学界自此历时达数世纪之久才得以克服这种混乱…… 当时在波斯,回教徒与印度有了接触。在八世纪时他们从梵文书籍中获得了天文学的初步知识。大约在公元830年,穆罕默德·义本·莫撒·阿勒——花拉兹米,一个梵文数学天文学书籍的翻译家,刊行了一本以后在公元十二世纪译成拉丁文,名叫《印度记数法》的书。西方正是从这本书中最初学得我们称为“阿拉伯数字”的东西,其实这是应该叫作“印度数字”的。这人又写了一本关于代数学的书,到公元十六世纪为止,这本书曾被西方用为教科书。”
罗素告诉我们,阿拉伯文化来自基督教会的发源地叙利亚(基督徒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叙利亚是被阿拉伯人以战争手段所征服。阿拉伯人只有一位“著名哲学家”,就是第九世纪的金第,而这位“著名哲学家”却连大名鼎鼎的希腊哲学家的名字都没搞清楚,翻译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却冠之以亚里斯多德的名字,而且这一错误甚至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如此的阿拉伯人能够传承什么样的文化?另一个闻名于世直到今天仍在以讹传讹的是所谓“阿拉伯数字”,其实那是“印度数字”——印度计数法。当波斯被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军队侵略并征服之后,波斯学者花拉兹米被迫离乡背井到巴格达为伊斯兰教当局效劳,他将原是梵文的《印度数字计算法》翻译成阿拉伯文,后来他的阿拉伯文又被翻译成拉丁文,这才真正在西方流传,也在全世界开始流传。所以,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对印度数字的剽窃和欺世盗名。花拉兹米的作品主要是以波斯和巴比伦尼亚的天文学、印度数字及希腊数学为基础的,与阿拉伯和伊斯兰无关。
对罗素叠叠不休一再声称的所谓阿拉伯人对亚里斯多德的重新发现和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所作的贡献,只要了解当时动荡危急的历史背景就可即刻戳穿他的谎言:所谓西方重新发现亚里斯多德一说,一方面是由于十字军东征开始更多地与东正教世界的接触和互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使基督教又一次面对回教统治下的世界中的异端对基督教的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出自伊斯兰教的“真理双重论”的异端学说。另一个重大历史变故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帝国彻底侵占,在这前后一个世纪里有大量拜占庭的基督教和希腊学者逃亡至意大利,很多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献和物品也因此被带到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由此激发了意大利对罗马和希腊复古的文艺复兴运动。

也就是说,伊斯兰教通过几百年持续不断的战争,迫使希腊学者们不断地向欧洲逃亡,从而使欧洲间接地保存了希腊文明。这就是罗素扭扭捏捏、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的伊斯兰教保存希腊文明的所谓“丰功伟绩”。

罗素为了支持他自己的这种说法,列举了两个为保存希腊哲学做出贡献的“回教哲学家”的例子。但可笑的是,第一. 这两个人都不是阿拉伯人,一个是波斯人,一个西班牙人,而这两个地区又正是被伊斯兰长期军事占领的“边远地区”;第二. 这两人最终都遭到了他们所生活之地的伊斯兰当局的无情迫害,以至他们的著作都被销毁,下面是罗素自己在书中的叙述: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有两位回教哲学家:一是波斯人阿维森纳,一是西班牙人阿威罗伊。前者闻名于回教徒,后者则闻名于基督教徒中间。……波斯人阿维森纳,他受到(伊斯兰)正统教派的猜忌,不时遇到麻烦;他常常要躲避起来,有时又被投在监狱里。他著了一部百科全书,由于伊斯兰阿訇们的敌意在东方几乎被湮没,但在西方,这本书的拉丁文译本却颇具影响。”
“而西班牙人阿威罗伊,他所有涉及逻辑和形而上学的书都被回教当局付诸一炬,阿威罗伊的哲学也因此在回教的西班牙境内告终,但阿威罗伊的哲学在基督教世界却传开了。”
即使从罗素自己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罗素所说的回教保存希腊哲学的途径,是将希腊学者在回教世界赶尽杀绝,使他们不得不逃到基督教世界,于是希腊哲学就在基督教世界得以保存下来。
正是由于阿威罗伊及其他伊斯兰学者的著作,产生了混淆亚里斯多德哲学和《可兰经》的所谓“双重真理说”。为了向伊斯兰教世界传福音,也为了在神学上回应这一对基督教信仰神学的挑战,经院神学家阿奎那写出了《反异教大全》一书。就像当年奥古斯丁因为要回答摩尼教和斯多葛学派对基督教信仰的挑战,以柏拉图的哲学为探索真理的起点一样,阿奎那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为回答这一挑战的起点。

而罗素则为了夸大希腊哲学,贬低基督教在西方的历史性影响,时而暗示、时而明言基督教中世纪两位最重要的神学家——四世纪的奥古斯丁和十三世纪的阿奎那,一位抄袭柏拉图,是柏拉图主义者;一位抄袭亚里斯多德,是亚里斯多德主义者: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基督教的神学和哲学,至少直迄十三世纪为止,始终更多是柏拉图式的而非亚里士多德式的。”
对此我只要指出两点就够了,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自己所说的话来回答。
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第十三卷中说:“我已经说了我认为必要的一切,用来反对那些以当柏拉图主义者为荣,或以被称作柏拉图主义者为荣的那些人……”
在第十四卷中奥古斯丁又说:“柏拉图主义者对灵魂和肉体的看法比摩尼教的观点可取,但也要受到谴责……” 事实上,奥古斯丁在他这本煌煌巨著的上半部(第一卷至十四卷),几乎全在论述希腊神话宗教和希腊哲学,他以纯净而坚实的基督教神学彻底摧毁了希腊哲学(和希腊多神论神学)这个以人类理性和幻想的谎言罗织起来的海市蜃楼。
而阿奎那则在他那本被罗素称为“将亚里士多德捧上基督教尊位宝座”的《反异教大全》中多次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谬误,因为阿奎那一方面要通过指出亚里斯多德一些正确的哲学思考与圣经真理的一致性来证明圣经是合乎理性的;另一方面,他也驳斥了亚里斯多德的很多谬误来显示和证明圣经的启示真理高于人类理性。我这里随便举两个例子。
阿奎那在他的《反异教大全》中指出:
“亚里士多德相信运动是永恒的,并且时间也是永恒的,但他的论证不是令人信服的……亚里士多德说,每一类事务都代表一种真实本性,而善与恶並不是同一属类,它们是不同的事物。”
对此,阿奎那反驳道:
“亚里士多德是根据毕达哥拉斯派的观点而言的,他们认为,恶是一种现实性,善和恶是属类;他(亚里斯多德)有引用当时貌似合理的观点的习惯。”
阿奎那显然反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善恶的观点而与奥古斯丁的看法一致:
“罪恶不可能表征着存在形式和本质”。“恶,指的是缺少善”。“一事物由于缺少它应该具备的完善性,就称为恶;丧失视力是恶,是就人而言,而不是就石头而言的。”
我不相信罗素没读过阿奎那就敢写西方哲学史,我也不相信罗素读不懂阿奎那就敢自称是逻辑分析哲学家,只是我相信,是他对基督教信仰的偏见使他变得愚昧无知。而且如果按照罗素自己的逻辑,奥古斯丁继承了柏拉图,阿奎那继承了亚里斯多德,那不就证明基督教才是真正保存了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与罗素讨好的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又有何相干呢?
罗素如此强拉硬扯,高抬希腊哲学,贬低基督教信仰,更使我觉得有必要澄清现代思想和史学界一个巨大的历史观念上的误区。今天我们所认识的西方文明完全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文明,而非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哲学为基础的希腊文明。但当我们说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源头来自希腊,并非是指希腊哲学(虽然希腊哲学在对解释和理解福音、认识上帝真道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主要是指:
1. 福音是在文化上希腊化(这其中当然包含希腊哲学的影响)的罗马帝国中首先传开的;
2. 希腊文字和语言是传福音最初几个世纪犹太和外邦人中最多、最常使用的语言;
3. 当时罗马帝国最权威的圣经译本(七十士译本)是希腊文本,
是因为这几个重要因素,才使得希腊文明成为基督教文明的源头之一,而不是因为希腊哲学。
况且,2000年来的希腊文明区域自身也早已完全基督教化,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希腊主要是基督正教(东正教)的希腊,而非柏拉图或亚里斯多德的希腊,90%的希腊人是东正教徒,而非是柏拉图主义者或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东罗马帝国(公元330年——1453年)的政治中心位于君士坦丁堡是希腊的古老城市拜占庭,希腊语自公元620年后成为帝国的第一语言(621年之前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东罗马帝国也被称为拜占庭帝国或希腊帝国。在拜占庭帝国时代,盟友和敌人都视其为罗马帝国(或新罗马)。全球东正教徒共有2亿6千万,这都是西方文明来自基督而非柏拉图最强大的证明。


宇宙观、人生观、伦理观高度一致的基督教信仰源自神向人启示的《圣经》而非希腊哲学,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常识。《圣经》中最早成书的《摩西五经》早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达1000年之久,罗素却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千方百计将一以贯之的基于新旧约圣经的基督教信仰传承任意切割。为了纳入后来的希腊哲学体系,将与《旧约》紧密相连的《新约》说成是从希腊东拼西凑抄袭进化的结果。这种荒唐可笑的说辞无非是无神论者篡改和歪曲历史的企图,是一种张冠李戴、甚至类似窃取他人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完全站不住脚。
历史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在面对希腊哲学全方位的挑战中,基督福音才最终彻底打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了希腊哲学,赢得了人心。《使徒行传》17章就专门描述了保罗曾在雅典天天与犹太人和希腊哲学家辩论,其中就有当时著名的希腊哲学派别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如果按照罗素毫无逻辑的说辞,保罗应该是去雅典请教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的大师如何建立基督教了。

当然,在一个文化上属于希腊世界的罗马帝国,第一世纪的教会教父们自然也同保罗一样,往往会以当时当地人们所熟悉的希腊哲学为起点来向人们阐明基督福音是如何优于希腊哲学,如此为福音争辩也是一个对希腊哲学进行辩驳、区分、吸纳和保存的过程。然而,希伯来圣经早于希腊哲学将近一千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罗素试图忽略这一点是一个诚实学者所不应为之的。
罗素表面看来十分推崇希腊哲学,但通篇读来就可以看出他不过是将希腊哲学作为取消基督教的借口而已,因为他自己在书中也表现出对自相矛盾的希腊哲学不以为然的态度。他无视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事实:希腊抽象缥缈的理性哲学和罗马严峻固执的法律秩序最终都匍匐归顺于基督教信仰,并非由于康斯坦丁大帝一时的冲动,也不是熟爱智慧的希腊哲人们的无知,而是因为基督教信仰本身所拥有的上帝超越性的真理及其对人具有圣灵感召力的属灵道德力量,而这正是希腊哲学所向往、罗马法律所缺乏的。
从罗素在书中常常对所谓“中世纪的黑暗”发出的谴责可以看出,他对基督教信仰所拥有的改变人心的力量茫然无知。他几乎将中世纪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基督教会和基督教信仰的头上,但却完全忽略甚至无视一个更伟大的历史事实:真正导致中世纪(五至十世纪)“黑暗”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大部分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在当时面临着来自哥特人、高卢人、法兰克人、伦巴第人、维京(挪威)人、丹麦人、诺曼底人、萨拉森人(穆斯林)等蛮族(未开化民族)长期的军事袭击和掠夺。而正是在这一中世纪长期的黑暗和痛苦之中,基督教信仰和欧洲教会才真正成为欧洲人精神和心灵的明灯!那些长期进攻掳掠欧洲的蛮族侵略者(除伊斯兰帝国入侵者之外),最终全都改邪归正,全都成为基督的信徒,并为欧洲日后形成强大的基督教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基督教信仰来自上帝具有改变人心的超越力量的明证。这也证明了罗素的盲点是何其的大。

哲学的希腊原文含义是“爱智慧”,是指人对宇宙人生的真理和意义进行的思考和探索;基督教信仰神学,是从上帝的角度向人类启示宇宙人生的真理和意义。从人的角度来看,希腊哲学的最高峰就是要到达上帝启示的真理;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圣经的启示正是要回答希腊和其它民族一切智者所提出的问题。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却拘泥于历史的表象,以“世俗小学”为傲,将圣经的智慧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结果读他的书就毫无获得真智慧的可能。
这令我想起早期教父特尔图良在第二世纪大声斥责类似罗素那样崇尚人的希腊哲学、却轻视耶稣基督福音和上帝启示的人,特尔图良质问他们说:“雅典究竟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