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哲学简史)(下)

指出罗素这位哲学家诸多显而易见、自相矛盾的错误,并非是要否定他所论述的西方哲学本身的价值和它们所代表的人类对智慧和真理探索的努力,恰恰相反,正是在全面考察了人类理性发展史之后,我们才能够在比较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认识到基督真理无比的优越性、完美的一致性和永恒的神圣性。
基督教信仰在罗马帝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在与希腊及其它异教文化的撞击中,以其强大的属灵生命力,改造并开创了欧洲中世纪璀璨的基督教文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又进一步促使人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学的巨大变革。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之所以没有指出西方思想发展史的这一显而易见的信仰或属灵层面的精髓本质,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他所叙述的历史现象,而是他不承认或是不愿相信这些历史现象发生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他会如此呢?我们来看看他在书中论及卡尔马克思的那一章就可以知道端倪。
“根据马克思的意见,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政治、宗教、哲学和艺术,都是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结果。这个学说称作“唯物史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尤其是与哲学史家有关。我个人并非原封不动地承认这个论点,但我认为它里面包含有极重要的真理成分,而且我意识到这个论点对本书中叙述的我个人关于哲学发展的见解有了影响。”
显然,罗素受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因为他“认为它里面包含有极重要的真理成分”,无怪乎他会排斥一切关乎信仰和属灵层面的因素,无怪乎他对基督教信仰的历史叙述不是归结于政治权力的争斗就是物质财富的累积,也无怪乎我如此熟悉他的叙述语境,因为我自己就曾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学生。
当一个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看历史,即使他还没有资格、机会和能力成为一个恶人的话,他也一定会成为一个唯物主义的盲人,一个无神论的庸人,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左派的那些人,他们并不明白他们所看到的历史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
比如说,罗素知道,“近代哲学的始祖、第一个拥有高超哲学能力、在见解方面受新物理学和新天文学深刻影响的笛卡尔”,他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沉思”,其实是源于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思想:

“圣奥古斯丁…是笛卡尔的“我思想”(cogito)的先驱。奥古斯丁在《独语录》中这样说:“你这求知的人!你知道你存在吗?我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是单一的呢还是复合的呢?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移动吗?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在思惟吗?我知道。”这一段话不仅包括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同时也包括了伽桑地的“我行走所以我存在”(ambuloergosum)的回答。因此,作为一个哲学家,奥古斯丁理应占据较高的地位。”
但是罗素却没有向我们说明为什么奥古斯丁这个比笛卡尔早一千多年、这个”黑暗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却会比“近代哲学的始祖、第一个拥有高超哲学能力“的笛卡尔”占据较高的地位”。
其实,奥古斯丁的“思”远比笛卡尔的“思”有着更丰富的内容。奥古斯丁的“思”是心灵对上帝的记忆、理解和爱,而笛卡尔的“思”只是对人的认识(即只是奥古斯丁的“理解”),却遗漏了奥古斯丁的“记忆”和“爱”,而这在事实上造成了现代哲学对“记忆”(包括自身意识、上帝记忆)和“爱”(宗教伦理)的长期忽略和遗忘。笛卡尔并没有注意到“思”之“现在”是与“记忆”之“过去”和“爱”(预期)之“未来”连在一起的,没有“过去”和“将来”的孤独的“思”,导致了“时间”的整体在现代主体哲学中的缺场,“在思”的人忘却了自己是受时空限制的人,最终将自己取代了“永远现在”的上帝,于是,他就不能“正当地”爱自己、爱邻舍、爱自然、爱上帝。与奥古斯丁深邃的神学思想相比,笛卡尔的现代“借用”和“发展”好像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拷贝。
再来看看罗素对“德国唯心论的奠基者、一般认为是近代哲学家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的时间观与奥古斯丁的时间观所作的比较:
“奥古斯丁不仅是康德时间论的先驱,他令人十分钦佩的时间相对性理论……比希腊哲学中所有的相关理论,更是一项巨大的进步。它比康德的主观时间论——自从康德以来这种理论曾广泛地为哲学家们所承认——包含着更为完善、更为明确的论述。”

虽然在具体比较奥古斯丁与笛卡尔和康德的哲学观时罗素毫无困难地看出奥古斯丁的深刻性和准确性超越于这些现代哲学的“伟人”,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体现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奥古斯丁之所以成为近现代许多重要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思想楷模和灵感来源,其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由于奥古斯丁的思想来源于罗素所不屑的圣经启示。

奥古斯丁不仅是笛卡尔、康德等近现代思想家的精神源泉,其实也是中世纪经院神学家们如阿奎那的先驱和导师,他更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神学思想的重要源头。而这一切只不过说明了基督教最严谨正统的神学思想不仅具有一以贯之的系统完整性,而且具有不断更新人类思想、变革社会的生命活力,正是她在不断地孕育、催发、影响并开启近现代人类思想的发展。
但是罗素不承认这一点,他就像一个睁眼瞎那样,对原本应该是他专业范围内的近现代基础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神学和历史性关系竟然熟视无睹,茫然无知。
“直到最近的时代,人们还满足于惊叹并神秘地谈论着希腊的天才。然而现在已经有可能用科学的观念来了解希腊的发展了,……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功于科学,科学在十七世纪获得了壮丽辉煌的成就。科学带来的新概念对近代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过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罗素,不仅始终没有以科学的观念解释古希腊文明出现的原因,甚至根本没有回答为什么十七世纪会突然出现牛顿,莱布尼茨,波伊尔,以及开普勒,为什么现代科学会在十七世纪会如火山爆发一样,爆出了一个新世界?
罗素是这样看待和评价在“科学大爆炸”的十七世纪到来之前几个世纪的历史轨迹的:
“文艺复兴时期(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除雷奥纳都及其他几个人之外,并无人尊重科学。意大利人在文化方面正经严肃,但是对于道德和宗教並不认真……”
在罗素眼里,十四、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十七世纪的科学发展无关,那么十六世纪呢?
“粗略讲来,宗教改革是德意志的运动,反宗教改革是西班牙的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的路德、加尔文…的思想认识和哲学观是中古式的。按哲学讲,宗教改革开始以后的一个世纪是个不毛的世纪,路德和加尔文重新回到圣奥古斯丁……”

罗素从民族地缘的角度而不是从神学甚至哲学的角度去考察宗教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得出浅薄甚至错误的、不合情理的结论。在罗素眼中,十六世纪是一个“不毛的世纪”,宗教改革只是一场“混乱”,这似乎是在说,他称之为人类最伟大科学发展的十七世纪是没有任何原因的。但这似乎又不符合逻辑。于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的罗素至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些事实:
“宗教改革开始时在知识界中影响十分不佳,但是…结果却是有益的……(它)扩大了…人独立思考的自由。由于宗教信条各异,因此便有可能靠侨居外国逃脱迫害。有才能的人…把注意力转到现世学问,特别转到数学和自然科学上。虽然路德的十六世纪在哲学上是个不毛时期,十七世纪却拥有最伟大人物的名字,标志着希腊时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这发展由科学开端……”
显而易见,罗素无法完全否认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无论好坏)也是十七世纪科学大发展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因为很显然,宗教改革不仅与科学各学科的创立和迅速发展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且在地域和信仰上也是密不可分的——早期最重要的科学家如牛顿、莱布尼茨、波伊尔和开普勒,几乎无一例外全都来自改革宗产生的新教国家如荷兰、英国、德国。虽然罗素对新教教会和宗教改革领袖常泼脏水,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
“幸亏存在有新教国家……(因为罗马的)异端审判所如愿以偿地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经历了几个世纪尚未复活。但是异端审判所并没能阻止(在新教国家的)科学家采纳太阳中心说,却给天主教会造成不少损害。”

如果说罗素因科学原故批评天主教庭对伽利略的异端审判尚属情理之中的话,那么他对向天主教会提出更深层次的神学批判、并由此催生了他所赞叹的近现代哲学和科学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的态度,就完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因为在这里一点逻辑都没有。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罗素要么是无知,要么是不屑,在这方面,罗素没有显示出一点思想深度。
现代科学脱胎于宗教改革,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现代科学基础的建立和各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仅仅是个人志趣天赋和才能的爆发,它是一个涉及整个国家社会的全面性系统工程,它出现的必要条件是:
1. 科学探索研究者对宇宙的认识有一种执着的、终生不渝的坚定“认知”和“态度”,那就是对上帝是造物主的信仰;
2. 依赖于一种对长期性的科学研究和探索提供支持和保护的环境,一种他人(周围的人)对自己所要探索的未知世界抱支持鼓励的态度,也就是他人的信仰与科学探索者的信仰是一致的;
3. 取决于权威机构在物质和精神上持久的支持和帮助,这包括教会和国家的作用和力量。而这一切条件的形成就是宗教改革所导致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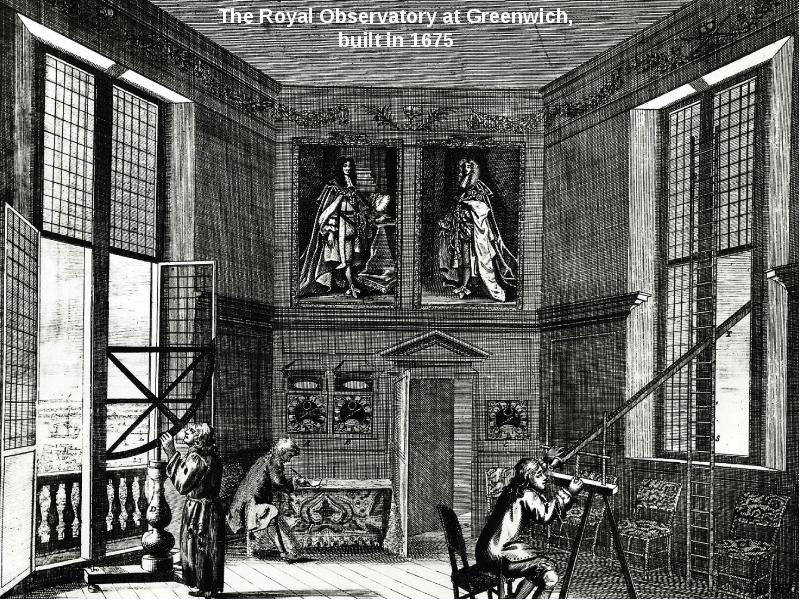
伽利略被定为异端是在罗马教廷为审判宗教改革家而设立的宗教裁判所的大环境中导致的,罗马教廷的本意并非是针对或定罪科学,而是针对宗教改革。身为天主教徒的伽利略与身为新教徒的开普勒关系密切是伽利略遭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与开普勒一起跟随路德的新教徒也支持伽利略,所以在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审判和禁书中也包括开普勒的著作。
而且十六、十七世纪那一两百年出现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来自荷兰、英国、德国等新教国家以及法国(法国是加尔文的故乡,是新教胡格诺派和天主教的必争之地,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使法国一度成为宽容新教的天主教国家),尤其是十七世纪的荷兰。罗素也注意到了这个历史现象:
“初期的自由主义是英国和荷兰的产物,带有一些明确的特征。它维护宗教宽容;它本身属于新教,……”
在罗素所论述的近现代哲学家中,笛卡尔是法国天主教徒,斯宾诺莎是西班牙的犹太人,但他们却都在荷兰度过他们大部分的人生。洛克是英国人,他也曾逃亡居住在荷兰。荷兰成为当年欧洲的避难所。最著名的英国清教徒五月花号航船就是于1620年起锚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渡过大西洋驶向北美洲的。荷兰也成了欧洲出版社,伽利略、笛卡尔、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等许多科学家思想家都曾在荷兰出版过他们在本国禁止出版的著作。荷兰之所以在十七世纪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宽容的国家,是因为她在十六世纪受来自日内瓦的加尔文神学的影响,使荷兰成为新教改革宗神学的大本营。1688年,荷兰共和国的威廉登陆英国,帮助英国完成了影响深远的光荣革命。而这一切就是罗素含混不清、隐晦的、消极的形式所提及的宗教改革对近现代科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发展的冲击力量:
“由于宗教信条各异,因此便有可能靠侨居外国逃脱迫害。有才能的人…把注意力转到现世学问,特别转到数学和自然科学上。”
人类历史上因为宗教信条的不同及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人类历史上有才能的人如哥白尼和伽利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把注意力转到数学和自然科学上,即使他们是神职人员;人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战争导致的逃亡。但是,为什么单单十六世纪会出现因为宗教原因而侨居外国?又为什么十六世纪的混乱和灾难却会使接下来的十七世纪成为科学上最伟大的世纪?
罗素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他也回答不了。
欧洲如果没有十六世纪在神学和宗教上的改革,就不会有十七世纪科学的大发展。十六世纪对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神学要义的人而言确实只是混乱,从表面现象看来却如罗素所说是一个“不毛时期”,事实上,信仰的更新孕育着人类思想和社会行为的更新,基督教信仰对自身的审视、改革和归正,是催生人类新时代的产前镇痛期和分娩期。

罗素对此当然并非一无所知,只是他摒弃了基督教信仰,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应用于西方科学哲学史,想当然地将科学看为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势,于是在现代科学的起源问题上就成了一个瞎子。
然而,当罗素这样做的时候,当他在为现代科学和思想发展发出“抽象理性”的欢呼的同时,对现代人类思想的具体发展其实也是失望和彷徨的:
“德国的优势是康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是普鲁士的哲学喉舌,为后来德国人的爱国精神和普鲁士合一崇拜作出了很大贡献……卢梭和康德之后分为‘冷酷派’和‘柔肠派’。‘冷酷派’从边沁、李嘉图和马克思逐步发展到斯大林;‘柔肠派’经过费希特、拜伦、尼采发展到希特勒……马克思是黑格尔的信徒,……在现时(1940年代)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浪漫主义的反抗从拜伦、叔本华和尼采演变到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理性主义的反抗始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哲学家,然后是英国哲学上的急进派,在马克思身上取得更深入的发展之后,就出现了苏俄。”

在这一点上罗素是对的,人类思想的发展并非天马行空,而是以历史的形式在不断延续。基督信仰经历了罗马斗兽场上的殉道、中世纪蛮族长期入侵的黑暗,才孕育出我们今天所享受的西方精神文明;宗教改革经历了欧洲秩序的分崩离析和混乱争战,催生出今天西方的科学、政治、经济及人文秩序;而之后出现的近现代崇尚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渐渐离弃了基督教信仰,最终却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纳粹主义和今天的左派全球主义,这是人类的悲剧。二十世纪人类在付出超过一亿人生命代价所学到的功课就是:人类的任何观念都是有后果的。
虽然罗素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代替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所导致的严重问题,但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时期对人类前景的看法,虽然无法摆脱左派特有的一厢情愿的学究气,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具有永恒价值的奥古斯丁的思想:
“现代世界就目前看来似乎正朝向类似古代的解决办法发展下去:一种通过暴力强加给人的社会秩序,它代表掌权者的意志,不代表平民的愿望。美满而持久的社会秩序这个问题,只有把罗马帝国的巩固和圣奥古斯丁‘神国’——“上帝之城”的理想精神结合起来,才能得到解决。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哲学。”
这种“新哲学”,不可能来自人间,只能是来自上帝自己的亘古常新的福音。
